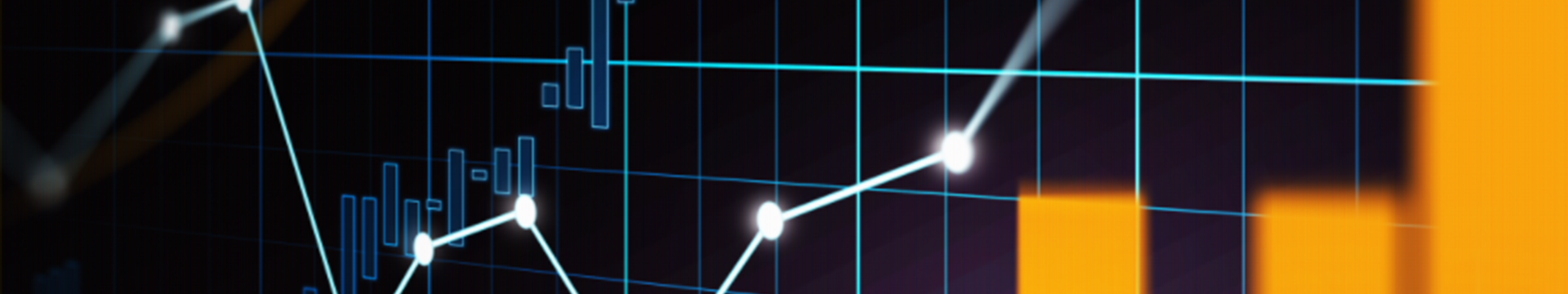傍晚時分,熙熙攘攘的順昌路上,又飄出了悅耳的薩克斯聲,那是王禮珊最拿手的《送別》。隨著建國東路68街坊及67街坊(東塊)征收首日97.92%的高比例生效,老街坊的居民們也紛紛用自己的獨特方式,和這片煙火氣十足的舊里作最后的辭別。離別之際,有不舍、有期待,更有溫情的感動……
今年68歲的王禮珊和姐姐,住在順昌路522號的江西飯店樓上,是這里的“老土著”。在順昌路上,只要提起這對姐妹,街坊鄰舍都會翹起大拇指,“太不容易了!這樣的姐妹情深,很少見!”
穿過順昌路522號一個油膩膩的小弄堂,爬上十幾級狹窄黑暗的小木梯,就到了王禮珊家。這些年,歲月的沉重,都鐫刻在王禮珊臉上,或苦、或累,或悲、或憂,坐在桌前的王禮珊向記者敞開了心扉。

姐姐三歲的時候,因為一場大病落下了病根,而后智力出現(xiàn)了問題,無法與人正常交流,身邊隨時需要人照顧。“父母健在的時候,我還沒這么累。”王禮珊說,那時候,她還在樓下開本幫菜館。“生意好額,她是這條街上有名的女老板。”建三居民區(qū)黨總支書記陳瑜對王禮珊一家也頗為熟悉。
隨著父母的相繼離世,照顧姐姐的重任就落到了年輕的王禮珊身上。“剛開始,我還不是特別懂。”王禮珊印象中,有件事讓她現(xiàn)在回憶起來都很“后怕”。“那時候,我?guī)Ы憬闳ヒ粋€親戚家‘白相’。去的時候,我們都是乘公交車去的。回家的時候,我突然想起來,我的自行車還停在南京路旁邊的一個小路上,我就把姐姐送上了公交車,并叮囑好她哪站下車,我騎自行車在公交車站等她。”王禮珊說,誰知,這個看似簡單的決定,卻釀禍了。
“我在公交車站等了又等,就是等不到她。天黑了,我又騎車來來回回找了好幾個街區(qū),都找不到人。”心急如焚的王禮珊滿大街找了三天三夜,還在報紙上登了尋人啟事,就是沒有回音。
就在王禮珊一籌莫展的時候,姐姐竟然滿身臟兮兮、一撅一拐地走回家了,“這三天,她是怎么過來的,至今還是個謎,我只知道她肯定走了不少的路,腳都磨破了。”心疼姐姐的王禮珊決定放下經營不錯的飯店,轉租給別人,這也就有了現(xiàn)在的網紅小店——江西飯店。
“生意可以不做,但姐姐身邊不能沒人。”此后,王禮珊就全天候地撲在了照顧姐姐身上。原本,姐姐睡在她隔壁屋里,因為擔心姐姐晚上起夜,容易摔倒,她就拉姐姐睡在了一張床上,“她睡床這頭,我睡床那頭,時時刻刻有個照應。”
王禮珊說,這輩子,姐姐就是她最大的牽掛,不敢生病、不能生病,單身的王禮珊就這樣強撐著,始終像爸媽在世一樣,悉心照顧著姐姐的每天。
幾十年來,樓下飯店的租金,就是姐妹倆唯一的生活來源。而如今,樓下飯店所在的建國東路街坊舊改生效了,姐妹倆的今后生活怎么辦?“你們家的難處,我們都知道。”建三居民區(qū)黨總支書記陳瑜耐心地勸慰著王禮珊。“我們的征收工作,一定會盡最大可能保障你們的權益,有什么困難,我們就是你們的‘娘家人’。”

在二輪征詢前夜,一直憂心忡忡的王禮珊同意簽約了。“舊改是好事,換個環(huán)境,我和姐姐的新生活說不定會更好。”談起未來的生活,一直堅強的王禮珊有點哽咽,“姐姐年紀大了,在市中心看病方便,我們準備在市中心物色一套小的二手房。”這一生,姐姐始終是王禮珊最舍不得、最放心不下的人,“姐姐萬一哪天走了,我會很難受,現(xiàn)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對姐姐好一點,再好一點,讓她像普通人一樣安享晚年。”

記者手記:
在1877權證的建國東路街坊里,王禮珊一家的故事,或許只是萬千故事里的一個小小存在。一個門店、一間小屋、一對姐妹,故事平凡而細碎。
但在與王禮珊的一個多小時采訪里,往事的回憶里始終流淌著令人感動的人間溫情。舊改地塊里,在一次次采訪中,記者見到太多這樣的場面:為了征收補償款的劃分,兄弟姐妹間或是爭吵不斷,或是直接訴諸法律,糾葛與撕扯讓手足親情分崩離析。淌著溫度的親情,就這樣“倒”在了冰冷的金錢面前。
但王禮珊和姐姐一輩子的深情,卻讓人看到了舊改的另一面。或許,舊改的“親情賬”和“家庭賬”,需要的是將心比心,以心換心。舊改,改的是環(huán)境,不能改了親情。因為,只要親情在、人情在,舊改的溫情就始終都在。